几何自然
张如怡作品语言的源头是最基本的方形、圆形、三角形或者矩形,画面以单个、成对、成组的形态构成,形式简练却细节繁复。她以理性的工作方法来控制并延伸个人化的视角,以及形式的表达逻辑,展览中呈现的作品,无论是单件的平面绘画还是在空间环境中散布延展的小型装置,始终具有对现实信息的过滤、删减、综合的主观意图,也是情感宣泄的提升以及语言节制等一系列动机造成的结果。
艺术家采用结构性的几何原则构筑绘画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的风格,它们充满着矛盾又极力弱化冲突,以此修正背景与物像之间相异的两重形态。其作品特征是多层平面的叠置,如同舞台场景充满戏剧性。通过透明感的色彩技术处理,透叠画面,常常以深色为底色呈现前景亮色的图像,反之或以亮色衬托暗形的拼贴画的贴图方式来转换前后角色的关系,绘画对她而言更像一种舞台化的布景实验。色调受计算纸和底纹的原有色影响,并不具有基本的对比色彩系统,仅仅为近似色。作品微观且细腻,需要近观。静物式的植物以及植物的变体充满隐喻,成为画幅中心位置的主要内容,微弱地塑造有限的体积。结构线的交接点、线上生成出异质图形,也是展现画面主体图像的支点。由于作品尺幅的限制使作品趋于平淡和温和,单件作品带有明显的局部性,每件作品只描述一个片段,却浓缩
成内容的精髓,组画形式无疑成为连接不同单元的合理组织要素,同时凸显出作品内涵上的连续性。
张如怡作品中的几何性带有理性平衡的规则,既强调构成推理又注重删减,空间与形状的压缩都是她进行从自然到几何的转化工具。审慎而理性的立场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领域并不普遍,成果也同样不够丰硕,也许正是其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静物的空间:张如怡作品回顾
“我们都将被这个世界规训,然而我们可以选择被规训的方式。” ——张如怡
张如怡在东画廊个展「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已于上周末闭幕。此次呈现的雕塑与场域特定的装置作品建立在艺术家长期在纸本的平面创作中探索可能性空间(possible space)的基础之上,继而依托一个建筑的视角,进一步在家庭/住宅空间(domestic space)的介质中制造楼、柱、门、窗等不同尺度构件之间的相对关系,以静物的坚定风格及凝练语言对典型的形式与有限的体积着手改造。张如怡于东画廊个展「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现场(2016):瓷砖作为一种常见装饰材料,通常出现在厕所与厨房。厕所是属于个人的绝对私密空间,然而厨房是开放的,能够触发诸多交流契机的地方。是次展览中,艺术家通过大量瓷砖的铺设,与具体的作品相结合,唤起观者对于家庭/住宅空间的怀旧情绪。而其栅格状的肌理亦与艺术家早期的平面创作息息相关。“温室5”(纸上综合材料,23×26cm,2011):艺术家在早期平面创作中建立可能性空间的基础并非西方自然主义的光学视觉结构而是中国山水画中的图形语汇与构图方法——沿着画面垂直线、水平线用一个斜顶或一座山的三角母题斜肩取来的对角线形成平行四边形,以提示空间的后退,与被安置的植物元素(主要是仙人掌)所象征的自然一同构成了“被工业化”的景观。
艺术家在近期实践中所使用的主要媒材是混凝土这一常见的建筑材料。作为工业社会中颇具代表性的人工制品(artifact),混凝土的主要成分水泥却是来自于砂、石等自然物。在将自然物转换为人工制品的操作中,艺术家开始质疑个人在物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工业化的外部条件如何聚集到一起而形成日常的秩序。因此,“转换”逐渐成为艺术家主要创作语言之一,被运用在雕塑与建筑的相互融合与纠缠中。“打开或关上”(混凝土、二手木门及钢筋,尺寸可变)、“重叠”(二手铁门,尺寸可变)与“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1”(混凝土与铁丝,19×10×15cm),「山中美术馆」,四方当代美术馆,2016:艺术家从南京当地的建材回收站寻得灵感,观察到了废弃的建筑与装饰材料是如何遭遇挤压和捆绑,并对从拆迁现场获得大量现成的木门和铁门进行了二次创作,沿用“封堵”的形式与其在平面作品中善用的线条语言对它们进行安置。
段义孚(Yi-Fu Tuan)称人工制品是需要运用技艺、调动知识及实践而制成的事物,它作为特定的工具在建筑情境中通常表现出控制的特点,既能够推动被认为可取的社会目的,有能够激发思考并深化自我意识。[1] 如果说混凝土在粗野主义建筑(brutalist architecture)中为形式主义(formalism)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提供了一个标准意象,那么混凝土在艺术家手中即从这样的固着状态中解放出来而编制起新的叙事线(a narrative line),用以生产均质化的、自我揭露的建筑实体——“社会雕塑”,使得本身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隔离(segregation)及特化(specialization)意识得到消解。艺术家一边以雕塑的尺度为建筑造型,一边以建筑的表皮为雕塑构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与城市主义(Semiology and Urbanism)〉一文中表示,城市话语的问题在于构成其话语的表述仅仅是一连串充满情欲意味的隐喻。[2] 艺术家用铁丝将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若干完全相同的建筑体块捆绑到一起形成面对面的毗邻与对峙关系,把“社会雕塑”渲染成爱欲的客体(erotic object),以此暗示作为建筑的楼在现代主义的话语建构中是如何被大量建筑媒体规训为观看的对象而遭遇失格。但更重要的是,“捆绑”这一行为本身所揭露的是后现代城市情境中个人空间经验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实在性(substantiality)及表演性(performativity)——愈是受到束缚,愈是得到愉悦。
此外,在是次展览中反复出现的仙人掌作为贯穿于艺术家各类创作中的母题,是艺术家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隐喻。仙人掌的根部十分柔软,表面的刺却是极其坚硬。在平面作品中,艺术家在悉心安排的栅格线条上篡改或扭曲仙人掌的形态,将其与不同的几何形状组合以并以此为中心延展出山、地等空间场景。在雕塑及装置作品中,仙人掌不再为讨论绘画语言提供线索,而是作为现成的自然物与人工制品进行对话。艺术家在人工制品的缝隙中为其规划出一定的生存空间,或直接以混凝土将其转换为人工制品本身,这种时而亲密时而疏离的态度即是艺术家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方式——通过“转换”的方式与客观现实提出休战,藉此不露声色地牵引出工业时代下个人所承受的压抑与慌乱。

Ran Dian|旁白的房间
一转眼,东画廊搬到复兴中路1333号的黑石公寓已经五年了。五年,这栋老楼的外墙可能又黑了一些,雕花地砖上的花纹可能又淡了一些,对面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从无到有、人气也又旺了一些。这个空间在二楼,是一套公寓。除了卫生间,整套房子的采光都非常好,每个房间都有窗户。画廊的室内是全白色的,木头地板,天顶和窗户的贴边都是优雅而老式的。于是,这所有房间作为画廊的展厅,既是典型的白盒子,又因其公寓住宅的结构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每次展览空间上的构造。
张如怡对工业网格绘图纸与仙人掌迷恋已久。在印有密集网格的绘图纸上描画,形成具有静物画特质的多层平面作品,或许需要个性里多少患点强迫症。张如怡大学先学的版画,后学的综合材料。她告诉笔者,“版画是一种极具逻辑且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见于她既往的绘画,又可从这次的展览现场想见(白洁齐整的展厅背后,让砌墙的师傅把砖垒直,让我们眼前水泥墙或水泥部件上的网格线都是舒服的直线,肯定是一件很费功夫、时间、耐心、受了泥水匠不少白眼的活儿)。在数十年如一日画十字的上海知名艺术家丁乙眼中,张如怡的实践秉持着理性平衡的原则,而他认为,“审慎而理性的立场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领域并不普遍,成果也同样不够丰硕,也许正是其(张如怡)探索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构造上的限定令人欣喜地在东画廊的最新展览中被打破了。原本进门就是敞通明亮的客厅,这次却迎门立起了一面顶天立地的高墙。墙面铺满了划成方形小格的白色瓷砖,墙顶离天花板留了极小的缝隙。这种贴砖,常被用于八九十年代中国水泥建筑的外墙,所以我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觉得自己没有步入室内、反倒是走入了一个户外空间。这种室内外颠倒错乱的感觉,与白色、和体感寒冷的水泥,贯穿了整场展览。虽然是步入了一个房间,但其实又是步入了某种异域的空间,比如反复出现的仙人掌,这种典型的热带植物,在这房间中似乎成为错乱现象的标记。这要看理性如何定义,用很多几何元素、以秩序和重复作为工作方法就是理性吗?(又或者这些特性普遍到不需要被简单地从形式或工作方法上被归类,比如不能一谈到格子就只想阿格涅斯·马丁( Agnes Martin)或蒙德里安 。)如果理性是对整体生活现实基于严谨逻辑推断的态度,那么在东画廊的现场,我所感受到的,是这被认作理性的肌肤之下、漂浮在白色中的网格及其间大量的空间留白之上、袒露出的一段长长的、持续的旁白。就像张如怡喜欢的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在其影片《第七大陆》(1989)中伴随着镜头里无聊而重复的日常生活的语调单调的旁白。如果旁白在电影与戏剧中给予画面与现场以声音,那么展览空间的空则是一种无声却仍给予空间音乐性的旁白。
张如怡是个上海小囡,八零后。她对水泥大楼与白色瓷砖贴面的借用,让笔者想起东画廊展示过的另一位与她同龄、一样是上海人的艺术家苏畅早期做的一些造型逼真的微型楼房雕塑。八九十年代特定的审美、或者说只为实用功能与标准化而定义的楼房设计所导致的审美缺失,在苏畅以临摹手法手工做出的超写实雕塑中得以重现,构成一种失衡的比例尺度,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既已熟悉的、甚至被快速淘汰的陈旧的城市空间。而在张如怡的现场,楼宇在写实的同时亦成为一种高度的抽象,就像她画中的线条与留白,是某种空间划分张力的结点。转身朝向进门的方向的右手边,通往第二个房间的门中间竖了一扇 混凝土门,只要不是特别瘦的人,都只能擦着它任选一边侧身进入灯光昏暗的第二个房间。混凝土这种材料,对张如怡而言,其很多成分来自自然的局部,却在今天被广泛地运用于“建设”,形成社会“雕塑”,它像是连接不同时间的庞大静物,包容着个体的“柔软”。比在客厅中对空间的构造更激进,这面竖在门中间的门,是对她“我所不能了解的事”(2011)及“隔 | 断”(2014)的进一步探索。前者,张如怡把上海虹口区的一处住宅空间的大多数门窗都用水泥封起来;后者,用立体的混凝土块填充门窗的位置,两者的相同之处,均是针对通道或门窗的阻隔、占有、拒绝,从而改造空间及身体在空间中的状态与感知。第二个房间,仍在混淆室内与户外:儿时石库门弄堂里常见的公用水泥水斗挂在墙上熟悉的高度,只是没接着水、而是灌注了大半缸浅色的、早已凝固的水泥;三面窗(与客厅里窗的位置相同,让人想到常见于中世纪宗教画的三联幅形制)前一个半人高的小方格白瓷贴面基座上,放着一个中等大小的鱼缸。鱼缸,又一个可以与水泥、白瓷砖、仙人掌组合的元素,水里沉着一对水泥做的面对面的楼宇模型,三条黑不溜秋的清道夫以“缓慢的静止”的状态生活在此。观者得到了一个活的景观、一个典型的、属于日常的景观,但在看着水中的楼房时,心中却会堵塞一丝莫名的窒息感。安德里亚·阿诺德的影片《鱼缸》(2009)是年轻的女主角向窒息的现实寻求释放的一种隐喻,这个被普遍用做喻体的意象,为展览提供了节奏上的变频。静止无声在这里被悄悄地打破,唯有鱼缸里的白色灯管的苍白仍呼应着展厅的日光灯。
张如怡在最后一个房间只设了一根包着小方格白瓷砖的立柱,上面露出一截光着。左侧的窗洒进天光,日光灯围着天花板固执地亮着。再一次,对室内与户外的成功反转,并完美地延续了整个展厅空间一以贯之的张力。行至此,笔者也就很有信心这将肯定不是一个光靠照片就能了解的展览,而是一个将空间现场性发挥出来的必须身临其境方得其妙的展览,也是一个充分利用并改造画廊空间、将之与创作无缝贴合、并转化为一种属于张如怡的空间绘画的现实之镜,一方可步入的看似普通实则异类的三维之镜。她对空间的介入手段亦是对这些现场作为实物的“雕塑”本身空间性的凸显,物与空间相衬之妙。谨慎的舒适,明亮的阴暗,单色的寒冷,压抑着却因此其实是饱涨的、试图宣泄的情绪。就像说水泥还是混凝土,本质上的同质与认知上的异质在这场有效的空间体验构建中展开,每一件作品都与另一件在前面这些形容词组成的共同场域中连接起来。对面的楼,其实是对面,其实是面,其实是你,其实是材料与空间所描摹的现实的种种细节,是多余或不够的光线,是线条与网格,是不再是东画廊的一个能让你在安静里生发出对现实空间更多好奇与疑问的现场。这时,白色瓷砖构成的网格开始在视觉上脱离它所依附的实体(混凝土的墙或部件),延展覆盖到周身的所有空间,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其衡量、甚或就是被它设计出来的。
这时,东画廊的窗也成了展览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元素,笔者不禁靠着窗往外望,将身处的这片寒冷网格与上海金秋清冽的空气联通起来,将这片无名的、用水泥的沉重与空间的错落所构建出的轻质的时间,与黑石公寓和复兴中路沿街数百幢楼宇(大多也都是混凝土结构)所亲历见证的记忆的时间交织在一起。正如张如怡会用“缓慢的静止”来命名其作品,我们或可感受其赋予静态以速度和时间感的把控力。

Flash Art|张如怡: 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
“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是张如怡继2014年的“隔 | 断”之后在上海东画廊的第二次个展。这个公寓展览空间就像是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空间一样:东画廊不仅的确是从一个公寓改造而来的,看起来,艺术家是如此地熟悉这个充满私人空间意味的场址,以至于众多作品几乎在房间中自然地承担起了某种日常性功能。第一个房间低处的混凝土香皂(《香皂》,2016)向观众指示了一种可能的入门仪式——洗手;高处被两块水泥板夹着的仙人掌似乎从来就在这里自然地生长着(《盆栽》,2016);大混凝土板和清道夫共生的鱼缸(《清洁》,2016)也就是那为生活带来情趣的“活物“;那个不接管子的、中间填满了瓷砖的混凝土水池子(《倒影》,2016)也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常用的洗手池;更不要提那几个水泥做的插线板了(《连接》,2016;《电船》,2016),以及貌似坚固了房屋结构的《柱子》(2016)。这个原属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得以回归至日常之中去。
然而,如果我们选择强硬地将这些作品与一种现代生活——而不是艺术传统——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是为了一种非现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准备的。不能用的香皂、不能出水的水池、无观赏性的鱼缸、不通电的插线板,这些工具共同意味着此处有某种生活需要被维持,意味着“生活气息”。这接近某种现成品艺术的定义:被拉入艺术范畴的、不可使用的日常物件,但张如怡这一系列作品和展览空间的亲密性加强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整体,“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安排了一种超越艺术-生活对立的生命。 这是此次展览的政治性意义:或许这种生命已经完全解决了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困境,或许这种生命对资本主义一无所知。这种生命就跟对混凝土的崇拜一样, 是虚幻地给予了关于“长寿”的承诺的。而对混凝土的崇拜是多么现代的事情啊!这曾意味着廉价而坚实的关于未来生活的希望,但艺术家在这里展示的生活——这种展示“生活”的方式让人想起那伟大的“厨房辩论”,一种通过讨论私人空间直接定义生命政治的尝试——并不需要任何希望。这种生活的特性就是灰色的无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六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是物不疵疠而年谷熟”[1]——或是某种灰色的、无器官的芭比娃娃。瓷砖的大量使用不仅有效地加重了空间的室内环境感,而且也以一种很显性的方式为作品主体添加了一种框架,就像是油画画框能做到的一样。通过规律、反覆地使用瓷砖,作品以一种更为服帖的方式与空间结合在一起。尽管这些瓷砖并不抢眼,观者可以想象没有这些处在背景之中的瓷砖(尽管在《倒影》、《柱子》等作品中这些瓷砖走到“前景”中来,但是这些瓷砖仍然是起着框架作用的。
在过去的写作中我们也尝试多次考虑内部框架的部分意义,而作用于雕塑或装置作品的内部框架与绘画中的内部框架同样重要:这种框架很好地以一种欺骗式的方式完成了消融内部-外部对立的任务,以至于我们几乎要声称这些房间在作品之内,而不是反过来),作品将变得粗暴,或者说,作品将直接地(尽管可能并不是自觉地)引用某种现代时期粗野主义[2]建筑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瓷砖改变了作品的性别,掩盖了或扭转了那些插入、突起、撕裂的动态。那件与可见性、可触性、隐私、性癖及高潮有关的《窥视》因此也变得“邪恶”了起来。空间与静物的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我来说,“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更像是某种奇异女性的肖像画。

ArtReview Asia|日常生活的疏离
一位年轻中国艺术家用匪夷所思的混凝土雕塑和各种装置深入探寻当代社会的孤立感、疏离和都市紊乱。
“您在东画廊这一方净土里真是流连忘返呢。”笔者说道。在张如怡的新工作室里,笔者正等着水开,在两个独特的杯物中冲泡咖啡。东画廊位于黑石公寓的二楼,黑石公寓是一栋不拘一格的1924年建民居建筑,位于上海前法租界的中心。此屋保留了其原有家居布局,展览被安置在以前的客厅、两个较小的房间以及连通客厅和房间的走廊里。去年11月,这些空间也是张如怡的个展“对面楼与对面的楼”的主展场。
张如怡并未将这些空间当成是既定的。事实上,她把同个房间的两个入口都封住了:一个入口用水泥封住整个门,门上留有一窥孔,参观者可以通过这个窥孔窥视仙人掌的刺,仙人掌是艺术家的二维和三维作品中常见之物,表征力量、坚毅和痛楚;另一入口被一对水泥门分隔成两个平行的狭窄隔断,中间捆有仙人掌,狭隘通道堪堪通过门中央。访客仍然可以从两边留下的空间进出房间,而艺术家在这里要传递的是一种舍离,背包太大要放下,外套太厚得脱掉,若有必要,还须屏住呼吸收紧腹部,缓步通行…
两年前,艺术家曾对空间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突破。在其个展“隔|断”中,艺术家用一块巨大的长方体形状封堵了其中一扇门(如同一堵墙在空间中穿梭),并用水泥堵住了所有的窗户。在公寓里放置这些巨大、阴冷、潮湿、有工业气味的土块给人一种疏离存在之感,并将艺术空间转化为颇具神秘而封闭气息的个体心理空间,微妙而又安静,与外部世界或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联系都似乎行将止息。访客在被邀请观察和审视这个世界的实况时还须关闭通讯。
张如怡是80后,出生于上海,生于斯,长于斯。她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接受的训练包括使用综合材料的版画和造型艺术,这也说明了她为何在艺术中孜孜不倦地追求有机和基于过程的再现。这一点,加上对表现空间心理的兴趣,让她时刻沉浸于雕塑之中。然而,即便艺术家的雕塑领悟与日俱增,但是广大艺术观众却首先对她的画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她在此流派的标志性作品是用铅笔和水彩笔在方形绘图纸上创作,并且通常以仙人掌(以三维空间表示)为主题。纸上的作品平静、细致、生动;在小而呆板的数学方块网格与铅笔线条之间灵动,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仙人掌刺带来的刺痛感。尽管这些作品在艺术市场很受欢迎,但艺术家仍然始终主要关注三维的、基于空间的创作或干预。
说回她最近的展览,有一件作品因将艺术家的二维和三维实践交相联结而显得尤为别致。这幅名为《盆栽》(2016)的作品由固定在墙壁上的瓷砖构成的二维平面组成(宛如用方形纸构思其画作),在作品左手边挂着一个花盆,里面装着一棵又高又直的仙人掌。用铁丝将植物捆绑在一起,然后夹在两个住宅楼房的微型混凝土模型之间。本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如《缓慢的静止》和《柱子》(均为2016年),均使用相同图案将楼宇,建筑或内部细节的多个微型水泥模型面对面地放置或捆束在一起。以此方式,艺术家在每部作品的相同部件之间建立了对话,但任何真正的实际交流的可能性却尚有存疑,因为在每件作品中,所有部件的正面(或对外的面)都被覆盖住了。
此次展览的另一个突出作品是《清洁》(2016)。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水泥微型建筑部件以及一些普通的清道夫(喜欢吃雕塑上生长的藻类的热带鱼)一起放在了鱼缸里(由荧光管和空间内的自然光照亮)。因此,这部作品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个长期不间断表演的舞台。雕塑(如果这个术语可以用来表达整个作品的话)不仅是表演的舞台,也是其中的表演者。
在理解张如怡的艺术时,构成“装修”二字的两个汉字是关键所在。其意是安装、建造、装饰和/或修理。张如怡是80后(通常出生于80年代上半叶),80后这一代人从小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他们来说,对建造、搬迁、拆除、改造和装修的记忆历历在目,并构成了他们身心记忆的重要部分。正是这些集体记忆和社会意义-特别是使用电子插头和插座、瓷砖和定制门等物料的室内建筑,已经成为张如怡艺术的重要符号。水泥也是一种雕塑材料,有时会被她用作建造材料(尤其是在“隔|断”中),以微型形式再现普通建筑,或大楼和日常物品比如门、插座、香皂(引入人体的存在并增加亲密感)的实体尺度。在英国西苏塞克斯的卡斯雕塑基金会(Cass Sculpture Foundation)周围的树林里,艺术家的作品《暂停》(2016)通过在英国古德伍德的新谷仓山(New Barn Hill)的树上和地上安装水泥插座,表达了艺术家对现代生活境况及其环境的深思。
张如怡是那些拒绝在其作品中简单援引女权主义话语的艺术家之一。
然而,其作品中某些物品的重复出现,如仙人掌及其棘刺、关闭着的(而非敞开的)或功能异常的门、堵塞的入口或窗户、有时用过的香皂,暗示了艺术家个人对社会变迁的情感或感受:痛苦、力量、压抑、对缺乏沟通、奢华、过度消费感的沮丧。这些感受当然是整个人性的一部分,但作品中的感性和浓郁的特质表明,她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更为柔韧。
虽然在其早期作品中已经多处可见此类特征,但在最近实践中,艺术家对独特个体的表达已经转向对一种普遍状态的勾勒。当笔者试图理解艺术家对人类情感及其在物理空间中的表达的持之以恒时,通过张如怡从中激发灵感的艺术家名单,包括多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雷切尔·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丽贝卡·霍恩(Rebecca Horn)和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笔者发现她与包含通过材料和空间型作品不断探索类似领域的诸多女性艺术家一脉相承。与这些前辈相比,张如怡的方法包括复制、重复和对制作过程的专心致志,而这当中再自然隐去或剥离人为过多的参与。正因如此,个人和建筑世界的压缩所带来的离奇感方得昭彰。

艺术世界|张如怡: 房间为证
疏离的房间、凝固的形状、均匀的网格、标准化的视觉风格,很容易让人给张如怡的作品打上审慎冷静的标签。张如怡称这种风格为自己的视觉价值观,在价值观的背后,既有对纯粹形式的理性研究,亦有对空间与结构在精神层面的寓意的敏感回应。重复、挤压、秩序、社会属性,人与生活如流水浮尘一般的关系在空间中静置,凝成坚硬的形体,身体的反应被房间的躯壳刻画为习惯。张如怡喜爱将房间作为工作对象,在这里,风景、视线、行动、触感、 劳作、选择等属于艺术家、屋主、观众与访客的一切意念和记忆,都无声无凭,唯有房间为证。
Art World:
你目前的个人工作室在哪里,何时开始使用的?你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室吗?
张如怡:
我目前的工作室启用于2016年, 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地点在上海一个居住小区,并不靠近艺术园区。之前的工作室和我的住处是合并在一起的,只有十多平方米。目前的 工作室功能是为我提供创作、观察、 思考的场所,去进行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甚至是还未开始的创作可能。不过在上海时,我也并不会每天都待在工作室。
Art World:
你本科阶段学到是版画,硕士阶段学的是综合材料。是什么让你的兴趣转移到空间和材料方面的?
张如怡:
我觉得这种兴趣始终存在,并不存在突然性的转移。版画创作方式中包含着重复、秩序、痕迹、多元材料等特性,使我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种观察和工作方式。在研究生阶段, 这种表达方法得到加强,我的导师也给予我足够的创作自由,这点很重要,也很可贵。
Art World:
你的创作落实到物理层面时会经常使用房间的门、窗、墙、砖、插座和日常生活用品,有时是用混凝土再造,有时是用现成品,这种创作的源头来自你长期的生活经验,还是出于 对创作地点这一特定空间的临时性的观察?你有什么特别的观察方式和关注点吗?
张如怡:
我觉得两者都有,经验所占的比例更多。经验的来源比较多重,有来自成长经历,有来自后天感兴趣的部分,还有电影与音乐给予的养分。比如说,我喜欢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的电影,尤其是他自编自导的《第七大陆》,电影描述了生活优渥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在面对生活和一成不变的现实时只能麻木地反应,在最后的结局中,生活在无形间成为这一家庭的“杀手”,但生活本身永远不会得到审判,不是吗?整部电影没有太多对话,只是通过镜头和物的定格将人物的情感的变化与遭遇慢慢渗透出来。我对于处于现实物质生活中的个体的自我意识中的情感变化比较在意。我创作的主线是通过人与人、与物、与空间(居室为主)、与自然世界相互指引与牵连而形成的内在作用力,将情感隐藏进物的背面,让物本身成为动力。
Art World:
你2011年的项目“我所不能了解的事”和2016年11月在东画廊的个展“对面的楼与对面楼”都涉及对空间的大幅度改造。我觉得你作品中的身体感是大于视觉感的,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在一个看似标准化的房间中,对通道和物品位置的改变,对电线、插座这些隐形设施的特写,突出了人的身体反应、生活习惯与规范化的环境之间的张力。你是怎么看待你作品中身体感与视觉感的比例或关系的?
张如怡:
单纯物理性的身体因素并不是创作时的首要考虑,我并不在意肢体本身。但材质转换和对空间的介入干扰,在结果上或多或少造成了某种观看体验。在作品呈现上,视觉感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是观看,其次才是阅读。这两个展览的概念一脉相承,前者更加直接,从自身出发,出于对现状的不安与迟疑,以门、窗作为起点,使用建筑工业材,用混凝土来进行阻隔, 喻示出抵抗与无力的姿态。在“我所不能了解的事”和“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之间,我还做了“隔|断”和“缝隙”这两个展览,对更大程度的体积感和对人的情感限制进行了尝试。而“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所展现的并不局限于对门、窗的改造,而是通过将不同的建筑楼房以面对面捆绑方式, 呈递出一种流动于美好意愿之下的悲凉。这个展览中的一切,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收集而来的信息,它们进行整合、转换,与人本身相关,但又无关。
Art World:
“我所不能了解的事”的创作地点是一户上海人家的家庭住宅里,当时你在居民家中用木板和混凝土封闭抹平了门窗,而且是亲自施工动手的,地上也布满了混凝土球,让人无法步 行。怎么会到居民住宅里做创作和展览的?标题是什么意思?
张如怡:
“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这个标题的意思来源于罗大佑的一首歌,他的这首歌词唱出了人和现实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的面对方式,有点讽刺,也有点无奈,无形中与我的迷惑有了重叠。当时有朋友租赁了那个房子,想做些活动,我受邀去看了现场,就决定直接把房间作为材料来进行创作,这也是我长久就有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从准备到施工,我工作了将近一周,搭建和封堵门窗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通宵,全部是由我自己和朋友两人一起完成的。地面上的作品是在上海大学的美院工作室完成的,观展的人可以从前院走入房间。人的移动和混凝土球的滚动会在屋子里相互作用,相互干扰。粗劣厚重的混凝土和人的皮肤会偶尔接触,因为展览在夏天,观众可以在屋内赤脚走动,另一面墙上展出了两张暂时无法实施出来的混凝土植物的手稿。
在矛盾之间寻找一种转换是我一贯的兴趣。在做“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之前,我就已经在使用混凝土了。更早的作品《强心针》,我用柔软的纱布制作成坚硬冰冷的医用注射器,这 就是一种转换,注射器最终“注射”在混凝土的墙体上,在这里生命体征的东西被抽离,剩下的是对“治疗”的荒诞回想。混凝土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复合体,并不仅仅来自它的颜色或触感,混凝土的成分是不同的矿石粉末,在今天它作为构建空间的重要工业材料之一而被广泛使用,它塑造的实体慢慢变成一个个现代文明的静物,包容我们最柔软和最坚韧的部分。我更看重混凝土作为物质本身的能量以及它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
Art World:
你是否喜欢这种亲身劳作的方式,为什么?你觉得这种像建筑工人一般的施工劳动和有明确艺术家意识的创作工作比如在绘画状态时,有没有相似之处?混凝土植物的作品后来实施了吗?
张如怡: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任何时候都是处于一种全身心的劳作状态。无论使用哪一种媒介,对我来说没有太多不同,因为我的平面作品并不是在讨论绘画语言。重复的线条、空间、秩序感、造型僵硬如同静物的植物(仙人掌),它们都是我表达框架的一部分。创作媒介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体现在具体实施时,平面作品是自己和自己打交道,而装置作品则需要我和不同的人的打交道。混凝土植物也已经实施有段时间了,单个作品的体量不会很大,植物主要针对的是仙人掌,它外表的刺与内部的柔软形成一种对比, 这两种状态间的缓慢变化也是吸引我的特点,它让我感觉到与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反差也有交集的一种对应。
Art World:
在东画廊举办个展“对面的楼与 对面的楼”,布展用了多久?有没有改变过方案?
张如怡:
布展前后共用了十天,展览中有大面积需要现场制作的部分,需要充分的时间预留。方案在大致的效果图确定后没有太多改变。这个展览比较花心思的地方是在想法上。其实很多人都是从我的平面作品开始认识我的,对我早期的装置作品和空间性项目了解不多。装置这一媒介要实现也需要很多条件,条件达不到,就只能把想法放在心里。经过2014年的展览“隔|断”和在上海安顺路一个菜场内的杂货铺实施的项目“缝隙”(该项目是“兼容的盒子”艺术计划中的一期) ,还有2016年在南京四方美术馆“山中美术馆”展上的三件作品和英国卡斯雕塑基金会的户外雕塑,这些变换的创作地点和空间给我很多启示。因此,在“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这一个展上,我希望展览的面貌是对我过去的一个总结,能完整呈现我的想法。
Art World:
这个展览有一部分雕塑是在雕塑工厂定做的,和亲自动手完成相比,你更喜欢那种方式?委托工人制作和施工,由艺术家最终验收,似乎可以去除作品中的情感温度,让物品和对象更平凡、日常、标准。
张如怡:
我觉得很难去区分哪些作品是工厂制作的,哪些是亲自完成,它们都是去实现作品想法的手段,更谈不上我更喜欢哪种方式。确实有一部分作品我自己在现实中没办法实现,需要 交由工厂完成,也不能说工厂制作的部分没有手工的温度。这取决于作品表达的需要和最终输出的效果,而不是为了制作的效率或喜好。
Art World:
你如何看待(个人专属的)工作室、创作现场、展览空间三者间的关系?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吗?是相互重叠的吗?如果它们是有区分的,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张如怡:
普通的理解是,这三者就艺术创作来说存在从内向外的顺序,时而模糊,时而重叠,没有定数。一般来说,工作室和创作现场是私密的,但在创作者的角度,两者有交集,这种交集体现在思维上,而非实体空间上。如果想要直观地了解艺术家的工作状态,那就与艺术家多交流,去艺术家工作室参观吧。至于说作品在工作室中或在展览中,在哪一阶段才算完成,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要艺术家觉得它完成了就是完成了。
Art World:
你在做这些空间改造的创作或展览时,是否考虑拍摄工作进程的纪录片,把纪录片也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如果拍摄纪录片,是否会让观众更注意到艺术家的表演性,而非空间的最 终状态吗?
张如怡:
我没有拍过,将来也不会。如果有人跟拍,我会不自在,我只有在工作时自己记录几张有趣的过程照片,也不会用于展示。我不是表演艺术家。
Art World:
如果你未来的创作依然非常倾向于以一个整体性的空间为创作对象,找到合适的空间是否不是一件易事?你是否会考虑去陌生异地寻找空间或驻留?你最近的一次驻留会做怎样的 作品?
张如怡:
的确是这样,目前的状况还没达到想找空间就能找到的地步。对我来说,有时是空间找到我,而不是我找空间。艺术创作需要机缘,陌生的地方会有陌生的文化,驻地创作也会带来很多无法预想的意外,我还是会观察和挖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就像我最近在苏格兰格兰菲迪酒厂的驻地项目,这里环境非常安静,四周绕山,但这份自然的幽静反而不会成为我的创作母题,这里的石头、树、风 只是属于这里,它们只有在这个“场”里才被显现出来,别人无法带走。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这里的人,我会经常去超市,在当地人的生活常态中挖掘可能。
Art World:
你的绘画创作和你的空间、装置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可以把你的绘画看作是一种虚构的空间研究吗?绘画对你来说更像精神性活动去思考空间与形状的关系,以绘画做记录,还是更像劳动用重复性的动作去填充你的一段生命时间?
张如怡:
我没有在意绘画的语言,绘画与装置是相互重叠的,都来自在现实生活中的收集、提炼、概括,都是用重复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对话。我的方式比较依凭直觉,注重实践,社会现实 因素也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慢慢浮现,与之前非常直观反映个人感受与物质转换的创作方式相比,如今我的创作在对冲突进行调和。
Art World:
在空间性作品中,你将空间实体的色调保持为工业化、集体化建筑的“日光灯白” 、“水泥灰”,但绘画作品的色调更丰富、饱满,这截然不同的两种色调的用意是什么?
张如怡:
材料本身会有带有质感,我没有特意安排。我几乎所有的展览呈现使用的都是同一种灯光,除了户外作品处于自然光下。我的平面作品主要以重复的线条来构建空间和造型冷静的植物,画面的色调不是首位的,通过未被预设的线条的重复而形成的单面颜色不在我的意料中,形状与空间始终是我的关注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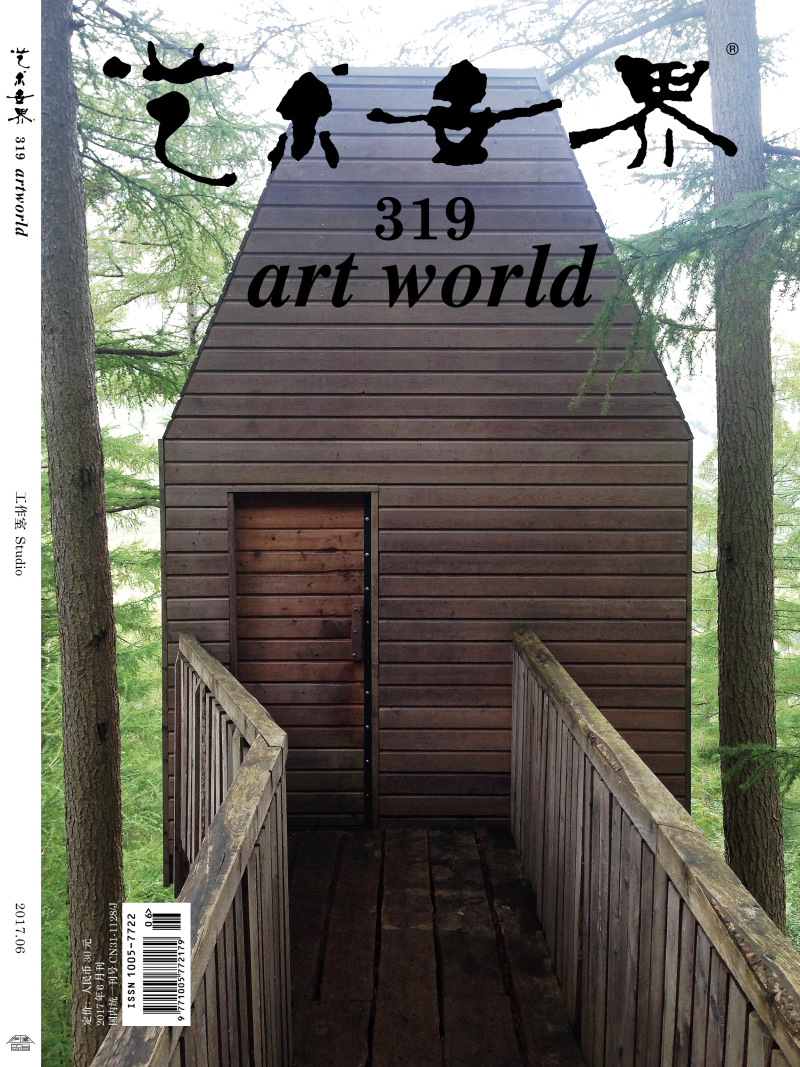
“轮廓”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 艺术探新
《輪廓》系某種在接受克服一個房間或任何室內空間的限制條件而為人工製品渲染出喜劇效果的方式,不僅重新建立起與居住環境的關聯,同時再次將藝術與建築結合。張如怡在其個展「對面的樓與對面的樓」(2016年)中就攫取了這種類型,并把它延伸到不同的機構脈絡中——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展覽「例外狀態」(2017年)與上海外灘美術館的展覽「行將消退」(2018年)里尤為顯著。在“裝修”的概念下,《輪廓》中的裝飾元素暗指適應於工業景觀的理性態度以及人工自然的準確規劃,而社會培養的屬性在這兩者之間構成了風格的基礎,藝術家在此成為一位城市栽培者。
《什麼和哪裡》,一扇常見於上海公寓內部的門被竪立放置並被分割成兩個部分,中間有鋸齒狀裂縫,象征內部與外部空間的相互滲透。
《這裡沒有燈光—6》,這幅畫展示了由手工牽引的規整線條與其他幾何母題疊加而成的複雜肌理,點狀個體由網狀的系統所控制。
《只有現在》,一塊被碾壓的建築碎片再次被瓷磚包裹,表面被植入仙人掌刺。來自於城市變遷的混凝土塊與仙人掌刺就像是自然中的山與植物。這件雕塑與出現在淋浴隔間中的地漏並置,意圖開啟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對話。
《一株-1》,一顆由混凝土澆築的異形仙人掌坐落在瓷磚覆蓋的底座上,像是被石化的植物標本。這件雕塑繼承了藝術家在早期紙本創作中關於自然物受到環境規訓的思考。

ARTFORUM五百字|张如怡谈“盆栽”
张如怡在洛杉矶 François Ghebaly 画廊的个展“盆栽”临时占据了建筑师François Perrin设计的员工办公室:一个在一千多平方米的庞大画廊空间里用半透明工业塑料纤维板和原始木材框架靠窗搭建的裸露式小型屋中屋。艺术家用两周时间在屋中砌了白墙,遮住原有的窗户和塑料纤维板。嵌有雪白反光瓷砖,同时如同建筑设计图纸一样带有网格的内墙面成为展览的支撑背景,而外墙原本的木结构框架则被保留下来。本文中,艺术家讲述了此次根据特定场域对空间进行的翻译和编辑。展览将持续到3月10日。
我希望创作一个跟现实拉开距离的时间和空间。
这次展览围绕建筑中的柱形结构和我用混凝土翻制的柱状仙人掌(cereus) 之间在工业化语境下的呼应展开。“盆栽”在中文语境里指普通家庭在泥瓦、塑料花盆内栽种的植株,往往不精致加工,即保留原生态又有观赏价值。这个思路跟Perrin的建筑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我想用盆栽做比喻来把内部细节放大夸张,同时把外部世界的景观浓缩,以此探讨当下人和社会现实、自然和工业之间的关系。
展览的英文题目“Bonsai”取自日语,原本的语义更趋向于精心设计、刻意模仿山水园林的“盆景”之意。François Ghebaly画廊的原办公室可改变余地很小。我需要根据它原始的空间设计来修改我的方案才能充分利用其结构和细节,并让场域设计跟物理空间、作品跟作品之间都有潜移默化的对话感,在此基础上再对空间进行新的翻译和编辑。这个小空间本来有窗户、两个门,和透明的塑料板墙,而且裸露式的墙高度不一,这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和机会。我用多层木板和石膏板遮住透光的窗和墙,再用瓷砖来呈现网格,以线和面之间类似透视的关系让墙面产生立体的物理感受,同时把三维的空间二维化,好比折纸或者在建筑设计网格纸上的绘图。这次布展我希望创作一个跟现实拉开距离的时间和空间,通过错位和矛盾制造一种张力,以此引导观众对空间的感知经验。我把其中一扇门的高度降低到进出要弯腰的程度;同时在另一扇门正中用砖红色混凝土按照真实比例浇筑了一根柱子,妨碍观众的视觉,而且使人出入时必须侧身。这根柱子一侧的螺旋纹暗示了一个无形的、不断上升的空间,而这个上升感又被门框给压制住了。在柱子同一侧的墙面上,与视平线同一高度处还有一个壁龛,里面放着建筑拆迁后废弃的混凝土残骸。我在上面一个很小的局部栽了一丛仙人掌的刺。水泥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工业建筑材料,但我们几乎忘记了它来源于自然界的岩石。水泥凝固后的冷静和理性气质很吸引我,而我对仙人掌的兴趣也已有几年了:它的自然属性—比如生长期长、表里质地差距大—给我许多灵感。我早期的纸本绘画构图里就已经出现过仙人掌和几何空间元素。后来把两者在雕塑中组合到一起时,我发现它们的结构和形态之间有很多潜在关系。
这个空间里最长最完整的白墙是靠窗的。我在它左下角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放置了一个真实的花盆,里边树立的仙人掌是用混凝土翻制而成,且内部和背面各藏有一根钢筋。这面墙右上方跟雪白的瓷砖高高镶嵌在一起的是染成砖红色的地漏。白天会有日光从地漏渗进室内。跟地漏对峙的是被压低的入口,观众低头进来需要仰视一个高高在上、光环一般的地漏。地漏跟矮门之间的瓷砖墙上略高于视线处是另一棵孤独的混凝土仙人掌。这棵隐含新古典主义建筑结构的仙人掌被两根平行的钢筋斜穿而过。最后矮门这一侧的墙面低于视平线处还有一块同为砖红色的舒肤佳香皂。中国最普通的廉价建筑材料—红砖的颜色把整个空间里的不同元素联系起来。而作品由于放置的高低参差不齐、距离不等而形成了相互作用,类似对位法的旋律配合,赋予空间一种节奏感。
最近两年,我的创作开始脱离室内和室外的概念,也试图模糊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界线。混凝土和白瓷砖的混搭使材料的反差和其暗示性被放大,也让观众产生里外错置的感觉。香皂、盆栽本来是人们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用品,但放到极度清洁的极简空间后,再从雕塑的角度对其形态进行处理,人的痕迹就消失了,只留下仿佛考古标本一样的陌生和缄默。瓷砖、网格跟仙人掌虽然在不同的墙面上,但又都在同一个构图里。我希望通过在视觉上处理线条与平面的关系让物体之间产生互动和对话,以此描绘一些用语言文字无法阐述的内在逻辑和态度。我希望观众的观看经历是一种从远到近,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借助对比和冲突发现生活和社会中平时注意不到的细微隐秘之处。

剩余物的诗学
从 2017 年开始,艺术家张如怡以多个关键词为切⼊点,通过⼀系列的展览,对“装修”这种⼈类的社会⾏为进⾏解构与重构。所谓装修,是指在⼀定区域和范围内进⾏的,包括⽔电施⼯、墙体、地板、天花板、景观等所实现的,依据⼀定设计理念和美观规则形成的⼀整套施⼯⽅案和设计⽅案。不过,张如怡的“装修” 系列⽏宁说是作为“装修”的标准定义的反命题提出,所要探讨的是被所谓的“装修”掩盖、排斥掉的那个暗⾯,通过具体情境的营造与设置,让平时被⼈忽视的、不可见的“暗⾊之物”重新浮现出来,促使观者不得不⾯对⼀个错位的窘境,从⽽对“装修”进⾏批判性反思。
“装修:碎⽯”是张如怡的装修系列中的第五个独⽴章节。碎⽯,意指建筑与装修过程中所产⽣的渣⼟、弃⼟、弃料、淤泥等建筑垃圾。顾名思义,建筑垃圾是⼀个包含了⼈类价值判断的⼀个表述,是毫⽆意义的、需要抛弃销毁的剩余之物。然⽽,这些“剩余物”并不因为⼈类的⼀厢情愿就从这世界上消失,相反,它们是作为建筑的镜像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并形成了某种强⼤的作⽤⼒,与建筑⼀起共同塑造现实中的时间与空间。那么,当我们⾯对⾃⾝所处的现实时空时,就必须⽤⾮⼈类中⼼论式的⽴场去进⾏考察。⽽“碎⽯”这个中性的表述,则凸显了艺术家在这个系列中所抱持的⾮⼈类中⼼论式的⽴场。
这次的房间(位于上海市中⼼的居室建筑)是⼀个仍然保持着剩余状态的空间,有着拆除之后的种种痕迹。残破的⽊地板、污渍的墙⾯、粗粝的⽴柱……形成了⼀种“剩余物”所持有的粗犷⽽复杂的空间语⾔。张如怡并没有简单地从⼀个主导者的⽴场出发对空间进⾏改造,⽽是邀请其他⼀些“剩余物”进⼊这个空间,与空间中的其他实体形成对话和撞击,让其中的⼒场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层次。 此次,张如怡在房间中央位置的四根⽴柱旁边放置了四台⾳箱,循环播放着她在不同室内外装修现场采集来的各种敲击、钻孔、切割等⾳频,这些声⾳此起彼伏、相互杂糅,⽆形中形成了⼀个声⾳矩阵,构成了⼀个强悍的实体。空间⼀处的⾓落窗台下,内置着⼀个单风⼜的空调外机,风扇的缓慢转动与声⾳作品⾥的“重⾳”完成⼀种反差。除此以外,房间⾥⼏乎所有的窗户被艺术家借⽤建筑拆迁时常⽤的廉价三合板遮住了透明玻璃的部分,每个单元格保留了极细的缝隙,对外的探视空间被压缩到了这⼀条缝隙⾥。
张如怡并不是对这些物理实体进⾏简单地排列和添加,⽽是将⾃⼰作为与这些实体⼀样的存在,去感受、体会、把握这些实体特有的语⾔和作⽤⼒,再以⾃⼰的⽅式,与这些实体进⾏对话,形成某种根本的相互依赖性。每⼀个实体的存在既改变了这个空间的性质,也改变了每⼀个实体⾃⾝的性质,从⽽形成了⼀个良性的秩序,合理地在时空中共存。
倘若我们回到这些实体本⾝,我们便会发现,这些被放逐的“剩余物”总是如影随形地萦绕着我们,⼀如我们那循环往复的、平淡⽆奇的⽣活⼀般。它们总是在不经意间以它们特有的⽅式提醒我们,宣⽰⾃⼰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只有摆脱⼈类中⼼论的框束,从这些实体的⽴场出发去感受它们的作⽤⼒,我们才有可能明⽩,虽然它们平凡⽽寂寞地隐匿在我们的周遭,但同样弥⾜珍贵,⼀旦我们合理地加以对待,它们就能毫⽆保留地发挥⾃⾝的作⽤。
在我看来,良好地与这些“剩余物”共⽣共存,是⽇常⽣活中被隐匿的⼀种诗学。这种良好的秩序是没有矫揉造作的形态,没有单⽅⾯的权⼒碾压与排挤,⽽是合理地成为⽇常⽣活的⼀部分。张如怡以这些“剩余物”的⽴场作为起点,在⼀定程度上将平时被光怪陆离的⽣活表象、不断膨胀的社会欲望蒙蔽的那种该有的良好秩序呈现出来。可以说,这个展览就是她对那种被隐匿的“剩余物的诗学”的感知与召唤。

流水洗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经历着都市景貌的急剧变化——旧的城市建设在爆破中夷为废墟,新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作为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艺术家,张如怡可以说是成长在“中国速度”的现代化建设之中的个体,她的艺术家工作也在试图复现并讨论这种建设与拆毁过程中个体与空间、个体于社会所存在的复杂关系。艺术家通过在空间中调和构筑物与立体创作、现成品以及建筑废料的关系,制造充满矛盾语汇的雕塑装置,展现现代都市环境中个体存在的境遇。
在“现代化石”的展览中,艺术家刻意调整入场的门径,用观看的动线将整体空间一分为二。进门后直面的墙体上略高于日常观看高度的狭小壁龛中摆放着一颗枯萎的仙人球,它被安置在由水泥翻模而成的蛋糕杯托中,灵巧且肃穆。这件被命名为《甜品》(2021)的作品,也许可以被视作本次展览题眼——它提示着观者整个展览将围绕个体的生长和人为的空间构筑而展开。
进入展厅后,在一片黑白灰的雕塑中,铺印在墙面上的橙色的计算纸网格显得尤为显眼。这些计算纸网格是艺术家大学时期的版画专业学习过程中提取出的元素,被广泛地应用在她众多的平面创作中,并进而演化为其雕塑的一部分和空间处理的一种方式。如放置于地台上的拼贴作品《记忆的荒芜》(2021-2022)系列中,艺术家手工将锡纸折叠成细小的方格并重新展开,以廉价的金属反光与手工的网格痕迹为作品打下基调,成为静物居留的空间。其上所打印的仙人掌图样和多种材质物品的拼贴,在被玻璃辗平压扁之后所呈现的随机状态,无不透露出一种人造的、廉价的、桎梏的紧迫感。从身体经验来说,这种生命体居住于同质性框架下的生存境况,直接影射一代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历史——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为改善城市中广大产业工人的居住状况而批量建设的楼房,采用了廉价的建造材料和可复制的简单结构。其设计语言深受包豪斯理念影响,强调功能性和可复制性、削弱审美和居住体验。可以说,“网格”作为一种视觉与生活的经验,确实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主义亲历者的感知中,成为意识形态的标志符号——成长于东德的昆特·弗格,即以围绕建筑的摄影研究和网格绘画系列,表现强大的社会秩序。在如今的中国,这种同一的秩序不再外显如人人同一的生活方式,却在紧急状态下严格的网格化管理中重又现形。网格,作为张如怡作品无处不在的背景,提示着此种压迫秩序的在场。
在张如怡制造的矛盾场域中,与挤压的力量同样强大的是与其对抗的生命力。《现代化石(管道)-1》(2021)中嵌在水泥翻模的PVC管道缝隙中的水泥仙人掌,作为生命体的代言,在管道的挤压中喷薄而出,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受制约的美感。更进一步,艺术家将有机体具有的生长性与流动性扩延至几乎一切的物。管道在日常生活中承载了排泄物的流动,如同汩汩的暗流一般出现在安静的展览现场,成为不可见物的显现。《日常配件》(2022)一作也延续了这种捆绑挤压的关系——水泥浇筑的蛋糕杯层层堆叠,如同罗马柱一般置于装修碎石之上,一根钢筋横贯其间,与一旁的现成品木条相比,其旁逸斜出的姿态呈现出一股野生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与项目空间有明显的依附关系:如《记忆的荒芜》(2021-2022)系列安放于项目空间原有的地台上,令作品平面成为地面长出的新皮层;《日常配件》(2022)则在空间本身的台阶上放置台阶形态作品,将建筑内含的强音拆分细碎。这些场域特定的装置,以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冲力,完成对空间原有秩序和功能的重建。
这样的实践可以回溯到她2016年创作的《盆栽》一作中,将混凝土浇筑的两个公寓大楼外墙用铁丝捆绑在一起,中间鲜活的仙人掌在坚硬的混凝土压迫下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动势。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逆贫穷艺术的一次讨论——它并非如乔瓦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 一般借助新鲜蔬菜的张力来维护雕塑的形态(Untitled (Sculpture That Eats), 1968),而是为仙人掌提供了一掊土壤以期生命的持续生长—— 雕塑形态的确立不被作为对自然生命力流逝的提示,而是被赋予了个体生命与人造物之间共生的证明。
在雕塑艺术的历史脉络中,女性艺术家的工作常常囿于女性个体经验(或肉身或精神),却长期被排除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之外(或被有意忽略)。而事实上,她们一直力图进入公共领域,拓宽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如伊萨·根泽肯围绕建筑、空间和大众生活创造的雕塑提供阅读城市、自然与材料的全新角度;菲利达·巴洛以废弃材料构建巨型雕塑介入社会生产-破坏-重构的机制议题讨论与自省。张如怡选择的符号(如网格、仙人掌、混凝土等)具有在坚硬与柔软间转换的可能,在制作方式上也使用具手感的缠绕和捆绑方式,呈现了一种兼具美感和张力的互搏关系,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感性气质。但同时,她从周遭的现代都市出发,以一种与社会伴生的直接视角,介入城市发展进程,持续跟踪并记录身处其中的情绪与感知。可以说,张如怡的工作试图超越女性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限制,也以一种更平权的视角,在城市不断更新的当下提供公共空间的更多想象。这种非人类中心的社会形态想象,从广义女性主义的角度提供了对城市和建筑的讨论入口。城市作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呈现,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秩序建构的伴生品。政府、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自上而下的构建我们现有的城市环境,而钉子户、流动小摊贩就如精心规划的景观园林中的杂草般成为需要被清除的对象。在父权主导的城市框架下,张如怡作品中越墙而出的植物代表了个体自下而上重塑空间的力量。于作品中,艺术家提出一种无限可能的开放性——在无往而不在的网格中挣扎着生长的植物,以强烈的生命情感呼唤着每一位观者,去共同探寻和创造一种更有机的社会组织形式。

“狡诈苔藓蔓生”
受灾星球的化石“Fossil of a Damaged Planet”,很难不注意到,张如怡近五年来的展览里面,植物的生命力愈发活跃。在她的不同作品中,透过猫眼、排水沟盖、管道、壁龛,各类型的仙人掌尝试从各种缝隙渗透入室内。它们的活力让人想到宫崎骏《龙猫》(1988)中栖居人类家庭的小煤球,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笔下的“狡诈苔藓”(cunning moss),也像是西普瑞安·盖拉德(Cyprien Gaillard)《夜生活》(2015)中的那棵狂舞的杜松柏树。在张如怡最近的“现代化石”(2022)展览中,入门即见壁龛上陈列着风干的仙人掌,形如海胆,底下用混凝土翻模后的蛋糕杯托着(《甜品》,2021)。在小腿高度的是个雕塑嵌合体《现代化石(管道)1》。混凝土的质感,统一了三种材料:蛇形水管的一头是麒麟多肉,另一边是球形仙人掌,它们缠绕在一起。同样是体内装载水体,这个奇特的雕塑组合暗示了多肉体内的80%水份能透过污水管联通两端的仙人掌,进行交换。
一个身体有两个面庞,其实,张如怡的创作本身也是如此:她的创作其中一张关于建筑的面庞反复被提及,然而还有另一面,是关于物种间的纠缠,只是比较少人深究。先从前一张脸说起吧。从她最初的个展“我所不能了解的事”(2011)开始,她便尝试着以展览为媒介,用改造展示空间的方式作为她的创作。这次展览中的《关于空间的梦游》(2021)也是这类型的作品,她将一扇二手木门的空心处,包括锁芯位置的圆孔,用混凝土填上,再用外墙马赛克封板。
张如怡确实很享受“把玩空间”的过程。一位看过她的画廊个展“隔|断”(2014)的朋友当时向我形容,室内的改造让他想起在家中寻觅横梁过道安装健身挂墙的体验——既掐得严丝合缝,也做出空间的翻转。在涉及建筑的这一面,人们往往关注她是如何唤起住家空间的细微情绪。一些论者称之为对特定日常时空的追忆之情。但仔细探究,怀旧所揣怀的时空源头却很模糊:是90年代京沪双城拆迁运动,还是2000年代,上海世博、北京奥运分别引发的市容改造,又或是2017年封墙堵洞的北京与2022年违法封上私人住居的上海?对我来说,这些薛定谔时空不过是再现层面上的表层关联,无意间反映了中国城市的诡谲时间感。真要谈及作品的核心,不该只是装修痕迹本身。我个人对张如怡作品的记忆,最早是当时在黑石公寓的“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2016),特别是用水族箱制作的一组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y)。水族箱自带LED灯,有点像是套娃一般回应展厅被堵上的玻璃窗和人造光源。艺术家向里面加水、养鱼,并将混凝土铸造的楼房形制雕塑浸泡在人造的环境里。用生态的角度来看,“环境”就在我们的内部,没有什么是外在于我们的。水族箱既是雕塑台座,也暗示了雕塑所处的生存环境。事实上,我们只要简单追溯玻璃水族箱的历史,便可以说明它作为环境建筑的本质。水族箱的雏形源自生物育养箱(Wardian case);1830年代,饱受空污困扰的伦敦市民以玻璃罩尝试为住家后院花园的植物提供密闭空间,隔开雾霾,意外地维持了植物的生命。艺术家后来也延续同样材料的运用,陆续制作了一系列以人造环境为展示基础的作品,包括《浸泡景观》(2019)和《幽暗的灯箱》(2020)等,显见建筑生产自然这一议题的重要性。而代表着驯化动植物成就的生物育养设备,其历史线索恰好反映了艺术家对此的理解。让我们进入雅努斯的另一面。张如怡最早的创作中就包括了一系列仙人掌的绘画。那时候,带刺的仙人掌更像是符号般的存在。艺术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投射,带有自传和解释学的特质。在这几年,她的作品开始更专注在植物在审美以外的其它面向,并注重植物和其它工业材料的互动关系。
在张如怡的个展“现代化石”(2022)上,两组绘画拼贴《记忆的荒芜-1》、《记忆的荒芜-2》(2021–2022)系列作品平放在展厅地面,水平向下探索垂直维度的纵深。在这两件作品中,转印在锡纸上的仙人掌图像有点像是贴了银箔的岩彩画、其它材料包括不同的铜丝网,有点类似装生姜用的小眼网兜、砂纸——它们被层层压在玻璃片下,形成形态丰富的不规则网格。取代了她以前常使用的那些横平竖直的网格稿纸。艺术家形容,这有点像儿时的玻璃写字台,为了保留珍视的图像,即便是皱了的糖纸花纹,也压到桌下。展开时,无意间制造了极其复杂的碎形拓扑纹理。
在《记忆的荒芜》的例子中,呈现玻璃压文件这一少女时刻的重点不在追忆的情绪质感本身。而是在追忆中意识到:这就是一个人最早能够动用的档案制作手法,并且根据这个档案制作者的耐心程度而出现不同的地质层次。而正是在这些文件性质的地质层理中,不同事物彼此交叠,暗示了生命相互缠绕的形态。
来到张如怡用厂房改造的工作室中,看见各种多肉生命在室内繁盛生长,一旁散落着柱形仙人掌的模具。比起绿植在她工作室中生生死死的各种形态,“现代化石”给人的印象着实有不小的落差:缝制在半透明薄膜上的植物的仙人掌尖刺,像是某种压花风干的技术,展厅中央的《日常配件》(2021)看似干枯的泳池地面,在展厅里唯一一株真正的植物则近乎枯萎。这样的反差让我想到喜欢用水搅动生命力的导演蔡明亮,在遭遇台北市大规模限水时,他的拍摄策略突然一变,陈湘琪吃外烩时餐厅不附例汤,也买无咖啡;李康生无水如厕,镜头仰拍烈日当空的画面。回头来看这次的“现代化石”展览,整场就属混凝土翻制的多肉植物和污水管长得非常多汁。就像是蔡明亮的拍摄手法,水循环以缺席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在十多年的创作历史当中,她的创作面貌也如植物般在难以察觉的长周期之间,悄悄地增添了重大的位移。工作室的仙人掌已经不单纯是艺术家描绘的对象,而是发生在艺术家生命里的陪伴物种。身处“现代化石”展场和艺术家的工作室,一枯一荣。我感觉,正是潜伏在水面下的这些艺术语汇,远比建筑/植物的二象性来得更复杂且有意思。套用一段《受损星球上的生活艺术》(2017)中的陈述,张如怡涉及的不正是“生态干扰的形态、纹理、颜色以及其模式”;“几个世纪的插枝、驯化、贸易、上税、染病,这些都体现在它们的结构和形态上。”这些被张如怡石化的多肉植物,它们的形态还在生长,看似要带艺术家去到更远的地方。
如碎屑一般
莫万莉(下文以“莫”代表):从展览标题“现代化石”聊起吧。为什么要用“现代”,而非“当代”这一更强调此时此刻的定语呢?
张如怡(下文以“张”代表):比较直觉地选择了“现代”。或许这是因为我所关注的并非是一个历史时段,而是现代生活框架下个体存在与情感状态的变化。在作为个体的人和现实之间,始终有一个微妙的矛盾性,存在着一种介乎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间的角力关系。我尝试通过物质、材料和视觉语言将这种隐秘的关系表达出来,把难以言说的抽象情绪状态,浓缩至如景物/静物般的作品中。
化石是时间沉积而来的物,这也是我理解“现代”与“化石”之关系的角度。一个时代所包含的一切事物,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调和—抵御—吸收的互相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生成的非物质的情感体验,借助它的残留之物得以证明。
莫:从展览来看,“现代”确实是一个更为适当的措辞。作为历史时期的“当代”之表达与19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息息相关,与那一时代的作品相比,你的创作显得更为克制,但“废墟”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你是如何理解“废墟”的呢?
张:我与那一时代的艺术家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吸收、消化、过滤,再呈递出来的面貌亦不一样。当时的艺术家,在外因的刺激和社会的改革中,更多携带了直接性的态度。我们虽生活在一个物质和信息更为密集的时代,却也不得不面对因这种密集而导致的压制。个体是时代的浓缩的倒影,作为思考和反馈的艺术创作,也随之变化。我更关注近距离状态下的疏离感,一种想要逃逸却不断限制的循环往复。为此,我的创作主要探索人、物料、空间之间的关联和层次,克制地调度了个体情感对于物质空间的注入。
“废墟”于我,并非仅是虚空的断垣残壁,而是包容(建),也是瓦解(拆),是更为弥久的“无形空间”之所在。它不是结局,而是“诱惑”我去更深入追寻的开端。我试图去“描述”城市生活与工业系统并置下的“碎屑”,它们就像渗透在城市的皮囊里一般,细小而尖锐。事实上,建筑(时代形态)与垃圾(剩余之物)中所隐藏的权力循环,无时无刻不种植在城市的任何一处。
莫:废墟化的过程把曾经属于“居室”范畴的“内部”暴露于“外部”的城市中,而你的创作又将它们再度置于“居室”内。你是如何理解这种“内”和“外”的关系的呢?
张:“内”与“外”的置换在我的创作中一直若隐若现,有时候甚至是不自知的。“行将消退”展览(外滩美术馆,2018)大约是第一次在和展览策划者的讨论中意识到了这种“内外错置”的特征,似乎通过碎石、瓷砖、猫眼门镜等中间介质的转换,可以将城市折叠和压缩至展览中。回想起来,2016年之前的“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香瓜侠公社,2011)和“隔|断”(东画廊,2014)两场展览,以“居室”为主,关注自我的观望和表达。“山中美术馆”群展(四方当代美术馆,2016)中的装置作品《重叠》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了走出“居室”的欲望。在这件作品中,我收集了不同纹样的防护铁门,堆叠排列,通过突出铁门纹样和框架侧边的线条性,来消解它们原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防御功能,转身为移动变幻的线条。如果说“门”是走出“居室”之欲望的隐喻,那么之后在“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个展(东画廊,2016)中,我将两座混凝土翻制的楼房模型面对面合并,用铁丝捆绑、悬挂于瓷砖饰面上。当处于“外”的建筑被挤压、缩小,属于“内”的瓷砖、装饰和日常的细碎被正视、放大、延展之时,“内外错置”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并在交替、转换创作途径中去唤醒个体与现实之间的关联。2017年开始的“装修”系列进一步走向“外部”的城市。无论碎石或是弯扭裸露的钢筋,这些物质形态所隐含的脆弱与暴力令我深受启发。它们就这样“名正言顺”地进入到我的创作语言中,获得了它们的角色——“现代化石”。
莫:这样说来,“现代化石”可以被理解为城市废墟的“居室化”过程。可以具体展开讲讲这一概念是如何在这次展览中呈现的吗?
张:你曾提到过巫鸿老师的《废墟的故事》,书中对于电影《小城之春》的评论令我印象深刻。片中人物关系在断垣残壁中的微妙处境,生活带给个体的情绪变化在城墙的边界上反复游走。“碎石”亦因残留的钢筋或是面砖痕迹,显露出那些曾经的微妙情绪,成为过去生活的倒影,就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提过,“在场”总是被过去和未来腐蚀,而它的核心恰恰是“不在场”。这次展览中的《甜品》、《记忆的荒芜1-2》、《关于空间的梦游》几件作品,也形成了这种与日常生活之现代性的关联及延展。
《甜品》这件作品的灵感源自2017年的苏格兰驻地项目。蛋糕纸杯是当地社交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日常物,带着欢快氛围的社会属性。被转换为混凝土后的纸杯,显得脆弱,而原本的蛋糕则被干枯萎缩为标本的球形仙人掌替代。“交流”的间距由此被调整,人和人的日常关系得到叩问。
正如前面提到我们正处于一个自我不断被密集的物质和信息所拥塞的时代,《记忆的荒芜1-2》恰恰借助了《装饰物》的挤压平面形式和空间中原有的两个水泥地台的因地制宜的结合,而构成了对这种拥塞作用的强化和隐喻。
或许展览同名作品《现代化石(管道)-1》是与“废墟”最为密切相关的。它的灵感源自2020年的铜仁路“装修:碎石”项目。在那个待“装修”的房子中,我偶然意识到隐藏于建筑内部的管道,正充当着一种隐性的连接和窥探之管,带来别处的声音和气味。这件作品选取管道局部与植物并置,将它们凝固为一块被丢弃的异形“石头”,展示在贴满马赛克的平面上,令城市的日常流动在室内停歇。
莫:提到《记忆的荒芜1-2》,我觉得展览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现有空间的结构与特征。
张:这次的展览空间存在一定的挑战。我试图通过作品的布置去调动甚至改变关于空间的体验。《日常配件》在现有的阶梯上创造了“台阶上的台阶”,与位于转角的《关于空间的梦游》的“门”互相呼应,激发走出“居室”的向往和同时被拒绝的尴尬境遇。我也将入口从正面调至侧面,希望形成一种更加迂回和含蓄的观看体验。
莫: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及调动可以说几乎完全重构了这一空间。这也是你在不同的展览呈现中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除了这点,“网格”也是你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元素。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曾在《格子(Grid)》中指出“网格”是现代性的缩影,它排除了一切叙述性和文学性,而通过高度秩序化实现了一种极致的纯粹视觉性。
张:克劳斯对“网格”的描述特别准确。我本科时期是学习版画的,这种媒介的制作过程繁杂而理性,但又充满偶然性。这段学习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重复、克制和痕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运用。
在早期的创作尝试在工业计算纸上描摹、篡改、扭曲我栽培的不同种类的植物(仙人掌)。借助网格的点位拉扯,形塑对象,将其过滤为不规则的抽象之物。之后由于在地项目的不断积累,仙人掌开始从“网格”中抽离,成为实在之物。与此同时,“网格”则以平面化的绝对形式出现在三维空间中,通过最为普通的建材物质得到转移。这次展览墙面上的丝网印制“网格”,是针对早期纸本(计算纸)绘画在现实空间中的拓展,也规范着空间本身,而展览中频频出现的瓷砖与马赛克,亦是被“网格”所“包裹”和定义的材料。
莫: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元素是“仙人掌”。在城市废墟中,正是植物最终占据了崩塌后的空间,并再度赋予其以鲜活的能量。但在你的创作中,“仙人掌”的塑造近乎克制,甚至会让人觉得比“碎石”更加内敛而克制。
张:“仙人掌”最为吸引我的特质,正是它的缓慢和距离。就像前面提到的,仙人掌在我的创作中经历了从物的图像转向物的实在的过程,而工业材料之于有机生物体的转换,令它的静默迟缓与时代的密度与速度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强烈。将仙人掌或是穿梭的钢筋作为整体,以混凝土进行转变,正是借助混凝土本身所具备的坚固与脆弱并存的矛盾属性,增加了它的沉默和克制。
莫:混凝土“仙人掌”最终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存在,将任何言说的可能性包裹于自身之中,而“碎石”则因残留的痕迹,以不完整的状态诉说着关于缺失之物的故事。

里昂双年展:《装修:空地》
“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赫塔. 米勒
<脆弱宣言>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它暗含着脆弱的隐秘和个体的离散,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中滋长、发酵、过滤,生成为一种态度,传递出一种声音。而这一态度和声音也同样隐现在我的创作观念之中。
个体与现实生活的对峙关系一直是我创作母题,通常以围绕日常逻辑而展开。作品也因调和人工制品、工业经验以及城市生活而占据特殊空间。我的创作主要涉及据地装置、雕塑及综合媒介的运用,牵引出现代都市中个体存在的晦涩境遇,并将其筑于物质之内,赋予物质之外的精神意义。
此次,我的项目<装修:空地>作为此前<装修>系列的第六个独立篇章进行展示,也是对之前系列的进一步探索与延伸,借由Guimet博物馆的特殊历史背景,让作品如同访客一般,完成会面,构建作品自身的对话感。前几年的<装修>系列侧重于在日常材料中涉取灵感,借现实为样板,调离个体、物料、场所三者之间的层次及相互作用力为主要叙述途径。在有机物体与工业制品的转化融合中,我试图寻找内与外的联系通道,以此建立个体与现实之间的“谈判”。这里的“空地”扮演着空无一物和堆叠废墟的两面角色,予我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吸引我去挖掘其角色背后的寓意。“空地”既是物理空间上的名词,又是心理空间上的形容词。在周而复始的城市“装修”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那些被遗忘的空地、那些被等待改造的空地、那些在内心被缺位的空地,彰显着它们自身脆弱的力量。

奇美拉空间
奇
空间无实相,她的每一副幻容都造化出新的异境。一处空间,是其外部裹据的广延及内部存驻的诸物之间共存秩序的综合。张如怡擅长制造冷致幽微的空间变相,以不动声色的错置和重复,将一方处所点化为不同材料与结构相斥相系、辩证嵌合的“奇美拉空间”。其中人形灭没,又人迹遍布, 有如人与非人杂处的交错群落。人手所栽所筑、与人朝夕共处之物活化为“物怪”,择处而栖,以形变示意(而非讲述)环境与物、物与物之间挤压出的共生因果。
物怪
“奇美拉”是希腊神话中由不同动物的部位嵌合成的怪兽。 张如怡的雕塑创作通过对日常之物进行材料置换与去功能性嵌合,孕育出一种既带日常气息、又脱离日常情境的“物怪”。
仙人掌是张如怡雕塑造型中的一个核心意象,也被她视为自我肖像的隐喻。仙人掌具有极强的储水能力,能在其他花木无法存活的干旱环境生长。其植株厚实挺拔,肉茎柔软却外生尖刺,纵使置于家居盆栽,亦带一股不容侵犯的柔韧。她以混凝土这一现代人居建筑常用的建造材料来翻制仙人掌的不同形态:在《角落-2》(2018)中,一根由拆迁废墟回收的钢筋从混凝土仙人掌多褶的肉间穿过,构成它的脊骨,高伫于布满瓷砖的柱顶,暗示楼起楼塌、生灭一念的都市环境中的个体生存境遇。而在《一株-2》(2018)里,倒伏的混凝土仙人掌上遍生绽开的导线,有如一块待充电的肉,静候渺无音讯的电能。两团相同的混凝土仙人掌构成《浸泡景观》(2019)的主体,沉于水族箱底,若两簇发髻并立,各有两条钢筋交穿,撑起同样的斜度。箱顶 LED 灯照出微弱的光,智能电热棒调控水温,清道夫鱼在两团仙人掌间穿游,构成一种有机生命与钢筋混凝土嵌合而成的“物怪”共栖的自足生态系统。
张如怡的雕塑物件还多选取人居环境中的日常用品,用混凝土这一惰性材料翻制,消除其实际功用,从而对现实的流通秩序进行微妙的局部阻断。这是张如怡独到的造物法,亦是她对加速现实的委婉干预。她作品里频繁出现的插座正是当代生活中被大量使用的流通端口。在展览“无序之美”(2016)中,她将若干混凝土翻制的中国插座“安装”在英国卡斯雕塑基金会林区的树干上,又把一个混凝土地插藏在基金会办公区近旁供人休息的草坪中(《暂缓,2016》)。被“暂缓”了现实之用的中国插座与人工栽植的英国草木不动声色地嵌合,使“物怪”出没于日常。在另一件作品《电船》(2015-2016)里,三只拆开的二手插头立插于混凝土翻制的多孔插板,插头内的螺丝暴露在外,昔日电流灼出的焦痕隐约可见。两条崭新的黄色导线将三只插头串联,同时弯出两道交叠的弧,与插板构成宛如船篷与船身的形态关系。这艘嵌合电船亦如一个小型“物怪”,暂停了它的日常载电,在无用的静止中航向未知的广阔自足之界。
网格
张如怡时常通过网格布造出一种“奇美拉空间”,即一种内生嵌套空间。它既围定边界又辟出维度,既是对空间中不同物体间关系的重构,又是对于空间结构与情境的再部署。
进入网格,既是置身于具体而日常的人居环境,又恍若从其间抽身,走进玄机隐布的空间阵列。张如怡的“奇美拉空间”要求观者经验与观念的双重渗透。在展览“对面的楼与对面的楼”(2016) 里,她首次尝试在空间中大面积使用网格,此展是“奇美拉空间”排布的代表案例。展览的原生空间是上海一套空置的老式套房,进门便遇到张如怡用方格瓷砖砌起的网格墙,这类瓷砖在上世纪 80、90年代曾作为上海公共住宅楼外立面的常用材料。通过使外部立面内嵌,隔断视线向内的窥延,从开始便产生一种外与内的倒错,并通过网格设下一种肃然冷寂的秩序。
物在空间中,又在网格里。网格是束物之网,又是物生之场。在展览现场一面方形白墙的正中,张如怡围出一块方形瓷砖网格区域,左半边悬挂着一株细长的活体仙人掌,夹在两栋混凝土楼房微缩模型之间,被一道铁丝困缚(《盆栽》, 2016)。在另一方向,张如怡在原先卧室入口正中垂直放入两扇翻制的混凝土门,门被上下两根铁丝捆绑,有如两块夹板,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活体仙人掌倒悬于其间的窄隙(《间距》, 2016)。卧室中竖立着一根网格瓷砖柱,由八幢相同的混凝土楼房微缩模型拼合成的结构构成柱顶,与天花板相接,“楼房”的窗面皆向内翻扣(《柱子》, 2016)。外与内的物被面对面地捆绑、嵌合,极端亲密又极端束缚。日常的尺寸关系被扰乱,物的人烟被网格缩影为抽象形态。张如怡的网格围布出一种整洁、压抑、诡异、惊悚的物的体感,亦指涉现实生活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挤压共生。
在另一个房间,一方网格被嵌进混凝土水槽之内,以凝固取代流动(《倒影》, 2015-2016)。然而,它同时又与其他房间中出现的或斜倚、或竖立、或支撑、或覆盖的网格彼此联应,构成一种流动变化的整体节奏,又似将整体空间的网格倒映其间。水槽托起网格,像戴着旧日瓷砖的面纱,亦如物的遗骸,收纳着旧宅之外流逝的光阴,封储它残留的余韵。
正
张如怡的“奇美拉空间”是一种有差异的重复,重复打开差异,使物分化,使其不溺没于一般性的深渊。她常选取样式重迭、却内含差异之物,以线性序列将它们排列组合,呈现出单个物件的特异性,又使整体产生出一种有序与无序相交合的变化。
在《流失》(2016)里,张如怡用许多同样的混凝土插座在墙上排开一道间距相同的序列,若干插头在插座形成的序列上无规则排布,被杂色的导线两两相连。仅用插座、插头、导线三个元素,张如怡就造出一个内嵌四组变量的复杂序列:插头的颜色、导线的颜色与形态、插头与插座间的关系、插头与插头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又彼此相系。整件作品产生出一种交合悖论:每个在序列中看似重复的插座因为其上插头的变化而成为独特,反之,每个在序列中看似相异的插头却因为插在重复的插座上而获得了某种共性。
《重叠》(2016)采用了相似的创作手法,它的组合元素更少,组合方式更简单:将若干来自废品回收站的老式铁门以相同间距、相同倾斜度焊接在两根相同的方管上。每扇门的大小、颜色、样式、花纹各不相同,唯一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被弃置的门。这些门如今已不再用于锁住什么,它们静静斜倚着,如一道斑斓的水波,亦如一个层叠的时光隧道。时间彷佛流过,“奇美拉空间”的出口正被打开。

近乎于无
在过去的10余年当中,张如怡凭借对材料语言的精准把握和纤细的感知,探索了以仙人掌和都市建筑为主的两条相互交织的创作线索。但当我们对这次展览中作品所运用的材料进行审视时,不难发现另一条鲜有提及的线索:不论是《浸泡景观-2》中包围在雕塑四周的玻璃,还是《沙漠并不悲伤,也并非无人居住》中附着在金属骨架上的塑料薄膜,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艺术家对于透明的标准化生产材料的关注。透明这种特性,隐含着洁净、规整、隔绝、控制与权力等诸多意象与议题。结合张如怡过往对建筑的持续关注,对其作品中透明性的讨论需要借助对建筑语言以及材料的思考而展开。
回顾材料生产的历史,玻璃的透明属性和其制造加工过程使之成为了一种隐含现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材料。19世纪,玻璃成为一种能实现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建筑用材,在尺寸控制上有着超高的标准,追求绝对的平滑和整齐。1851年,作为世界博览会场馆的水晶宫在英国伦敦的南肯辛顿落成,这座通体玻璃的雄伟场馆被视为该材料在建筑领域的一次突破。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接近5年的流亡生涯之后曾造访伦敦,这座以钢筋为骨,以玻璃为皮的文化“温室”让陀氏大为震撼。在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关于伦敦的章节中,陀氏写道:“它(水晶宫)是如此庄严、恢弘和豪气,以至于你开始喘不过气来。” [1]而这一章的标题“巴力”——希伯来神话中的邪神——则直白地说明了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态度。他直觉般地意识到这座玻璃建筑所蕴含的那预言式的形象和纲领性的隐喻。
彼得·斯洛特戴克在《资本的内部》一书中继续了陀氏对水晶宫的剖析,将水晶宫所代表的玻璃建筑样式看作是现代性最终极野心的象征——“创造一个人们永远不会离开的地方,一个包围一切的领域。”[2] 如今,优质的玻璃在平滑度和纯净度上有了质的提升,透明得几乎隐形,让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区分在视觉上愈发模糊,而在物理性质上则愈发坚轫。玻璃可以被看透,但无法被穿透 ;透明的结构看似隐形、包容,却始终维持着一种“有礼节”但绝对的阻隔与孤立。玻璃的透明性是自由、开放的,却也是欲图掌控,乃至专制的,成为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写照。就如同杰里米·边沁的全景监狱,一切都公开、可见,除了权力自身。
伴随着各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这种西方的现代性欲望同样进入了中国。作为在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成长的一代,张如怡在2016年的作品《清洁》中,将现代商品住宅模型浇筑成两件雕塑,相对而置,浸没于水缸中,黑色的清道夫游于其间。白炽灯泠冽的光线以及整件作品多重笔直的线条所散发出的秩序感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雅克·塔蒂的电影《玩乐时间》 (1967)。影片中充满了导演对玻璃这一建筑元素的敏锐审视——与空间材料有关的一切都被道德化了,无处不在的玻璃幕墙,层层嵌套的玻璃办公隔间暗示着现代都市空间的疏离感、重复性及其对人的规训。不同于塔蒂作品中富有讽刺意味的压抑与冷峻,张如怡在自己的作品中留存了一丝温柔反叛的可能性。玻璃缸中的水填充了混凝土雕塑的空隙,随时可能将这些小型楼宇溶解、侵蚀;但水在整件作品中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感,以至于艺术家甚至没有将其列入作品材料中。 同时,在作品中水和水箱边缘形成的三棱镜结构也揭示了透明性可以是一种视觉误导。我们的所见并非真实。
在张如怡2019年创作的《浸泡景观》中,艺术家继续了有关透明性权力关系的探索,但将作品的核心引向了生命领域。两件由扭曲的仙人掌与钢筋组成的雕塑浸没在装满水的玻璃缸中,作为有机物的仙人掌和无机的钢筋在混凝土的浇筑下得到了形质上的统一。这两者的结合,化身为某种远古异域生物,在透明玻璃水缸与没过雕塑的透明液体的加持下,被赋予了生物学标本一般的质感。然而,水在其中并非扮演着福尔马林那样的保护者的角色,而是再一次充当了革命性的温床——随着时间推移,水的浸泡让混凝土雕塑上长出了青苔。在作品展出期间,似医院般洁净、通透、被充分规训的景观被青苔的缓慢占领所打破。
透明性与生命领域的交集并非偶然。19世纪时,路易·巴斯德使用玻璃制实验仪器发现了微生物,同一时期出现的X射线成像技术(使皮肤和肌肉变得透明可见)和用于培育植物的玻璃容器沃德箱,已然将透明性的讨论引向了生命政治。
到了20世纪后期,工程师约翰·P.艾伦在1987年带领团队开始了一项极富野心的科学项目——生物圈二号工程。在这个由超过一万块玻璃搭建成的巨大金字塔形建筑中,设计者通过整合七个“生物群落”——雨林、热带草原、沙漠、沼泽、海洋、集约化农业和人类,试图还原地球——生物圈一号——的复杂生命支持系统。生物圈二号大量运用玻璃,为的是解决该建筑“物质上封闭,能量上开放”这一对几近于不可调和的要素。建筑结构被要求尽可能密封,以减少内部和外部的大气交换;但又要保持最大限度的透明,以最大幅地增加光照,来支持内部动植物的生长。然而,如同张如怡作品中令人意想不到的青苔,在生物圈二号工程的末期,藤蔓类植物沿着钢结构扶摇而上,阻挡了阳光,从而间接造成了热带雨林植物的死亡。
生物圈二号工程本身的透明结构可以看做是一个上演实境秀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柜。 如苏格兰国立博物馆馆藏总监塞缪尔·J.M.M.阿尔贝蒂所说:“就像活的动物和植物被培养的过程一样,当非生物/文化的产物进入博物馆,进入某类收藏,以及在它们随后的(来世)生活中,都受限于一系列的概念、分类和重述手段。……城市生活,像艺术一样,在玻璃背后的构筑中被净化了。”[3]从科学家的实验台到美术馆的展示柜,从细菌观察皿、动植物标本到人类的终极欲望——生物圈二号工程,玻璃作为一种介质、一个容器,承载了被观察和培养的对象,通过对内部的隔绝与透明化实现来自外部的审视,逐步定义着观看者与被观看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2020年的作品《低声细语-2》中,张如怡对透明作为一种区隔手段的关注无疑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巨型的半透明塑料薄膜悬浮在空中,随着窗外的光线和空气的流动缓慢而无声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当我们走近作品,能发现平滑的塑料薄膜上布满了仙人掌的针刺,这些刺穿透了塑料布,借由摩擦力悬挂其上。刺的尖锐消解了平滑的塑料布所象征的顺从,却也消解了触摸的欲望与可能。
在生物界中,动物以鲜艳的颜色、锐利的尖刺、具有攻击性的声音进行自我保护与防御,阻隔外界的危险。这些手段是直观且本能的。而在无机材料的世界里,隔绝却以一种看似洁净无害、平滑柔顺、开放可观的形态被呈现,只有当真正试图去触摸的时候才感受到这种对交互的冷酷拒绝。不同于仙人掌的刺或动物皮肤上的毒液,玻璃和薄膜其实是可以被轻易破坏的,它们近乎于无的材料属性并不坚固。不论是家门上贴的封条,绿化带前拦起的白色胶带,抑或是乘坐国际航班时避免交叉感染的塑料薄膜铠甲,它们的存在不是物理性质的隔断,而是指代权威的不可侵犯性。你需要自己判断跨越这条可以轻易被解除的屏障后续需要付出的代价为何,这一点是透明性最本质的威胁。
这篇短文以张如怡的创作以及材料语言为起点,希望为读者引入一个跨时空与学科的对话空间。张如怡的创作向我们传递了当代视觉艺术家们的创作与形形色色的理论和领域之间平行的关系,正如詹明信所言:“你从美学出发,纯粹的美学问题,而讨论到最后,终归回到政治。”[4]。因此,文中的政治不应做狭义的理解,而是关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纠缠的状态与演化。
[1]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满涛(译):“第五章:巴力”,《冬天记的夏日印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8-90页。
[2] 彼得·斯洛特戴克(著),维兰德·霍本(译):“第33章:水晶宫”,《 世界资本内部:迈向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剑桥,Polity出版,2017年。
[3] 萨缪尔·阿尔伯蒂.J.M.M.: “在玻璃之后构建自然”,《博物馆与社会》,第6卷第2期,2008年,第73页-97。
[4] 詹明信,伊恩・布凯能:“采访张旭东”, 《詹明信谈詹明信——有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